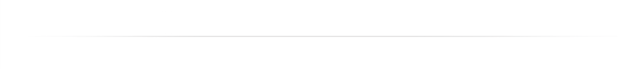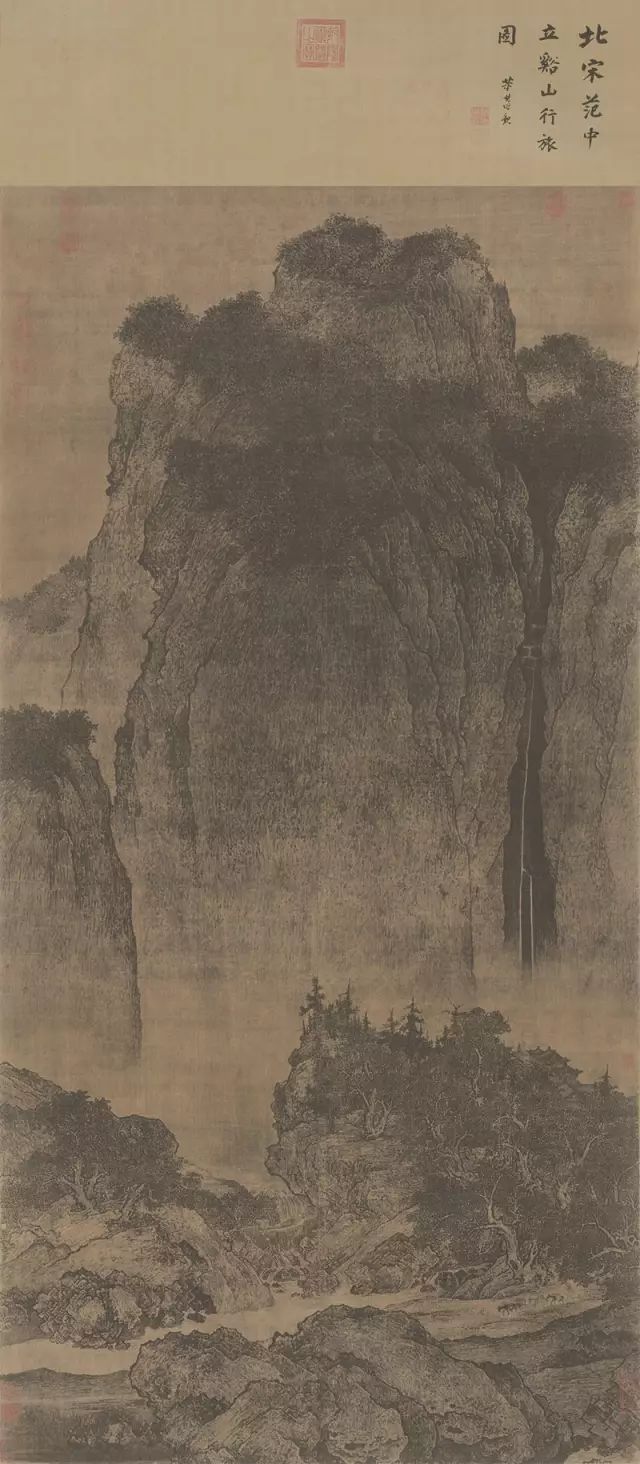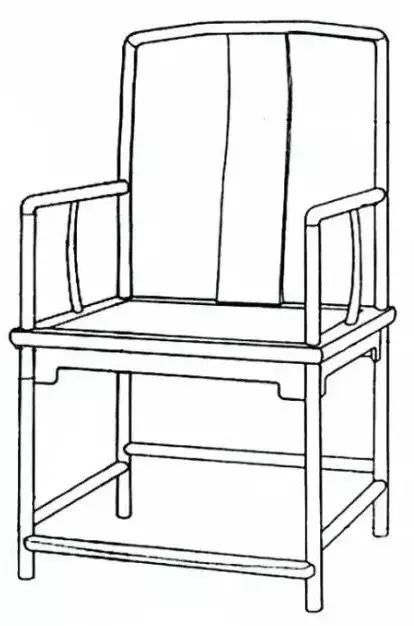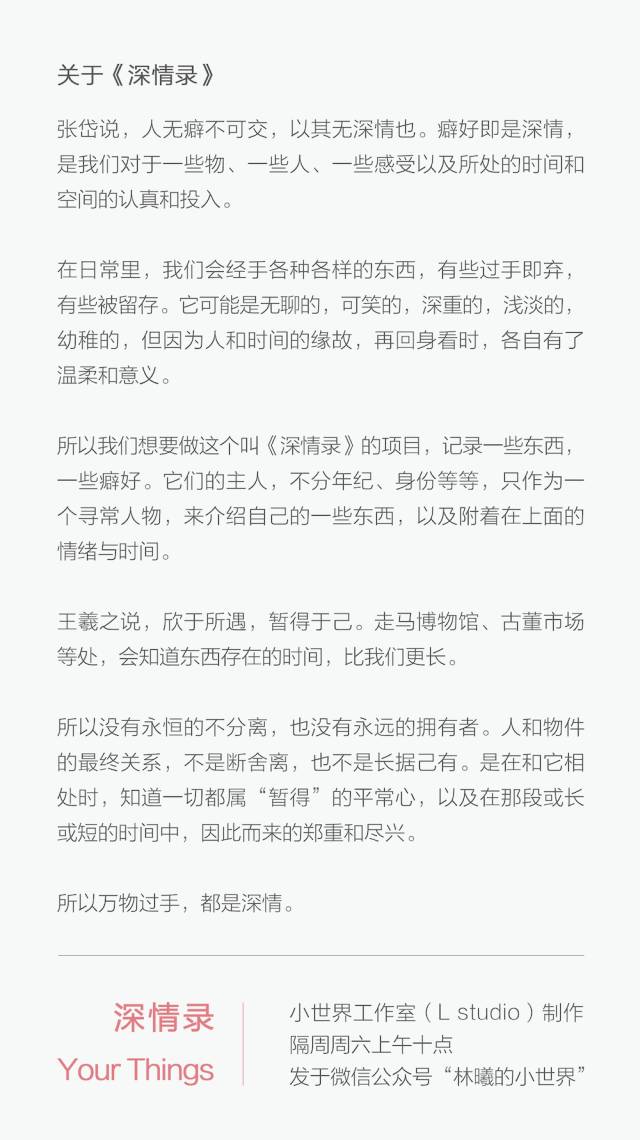中國人現在應該思考的是,為什麼這麼喝茶 – 王愷
王愷
媒體人、日客直播總編輯、活字文化新媒體總監,原三聯生活週刊資深主筆。對生活方式有深入瞭解,著有「文藝犯」、「浪食記」等,主編有「茶之道」,「香之道」。
王愷:
我就隨意開一個話頭。首先講講我看見的日本茶道美學。我前後去了很多次日本,而且是專門看博物館,茶室,包括現代的新出現的茶空間,只是不涉足茶相關的生意、不收藏茶道具和參與拍賣會一類。
我常去的地方是博物館,比如看千家的三個流派、煎茶道流派也看了很多,這裡可以接到曾老師剛才說的話,我認為大家過於注重區域劃分,比如大家一看到什麼,就立刻判斷這是台灣風、這是大陸風、這是韓國風等。在我看來,這種分野在非常快的時間內就會改變。我認為整個茶界的影響是螺旋式的、不斷地交換營養、交換對茶的認知。

為什麼中國會發展得比較快?剛有一些批評,像是葉老師描述茶文化成為顯學後出現的一些亂象,我認為這是因為茶文化的發展被中斷太久了,好比一株很久沒澆水的植物,一桶水灌下去都會喝掉-正因吸取營養的力量非常強大,許多雜亂的東西同時就會摻進來。好比說從台灣吸取某種形式、同時也從日本接收了大量的茶道具,或者從中國古代典籍中發掘不同的東西等,可最顯著的問題並非吸收了什麼,而是下一步大家不知道往哪走?
我不知道台灣現在的情況,從剛才何老師說的,或許和中國有點相像。中國在兩三年間走完了台灣可能用了二、三十年走完的路,現在不知道往哪走。現在看到無數的茶空間和茶人,大家都學了表層的東西,比如說做一個茶席、茶空間後再喝個茶,這個淺層的模仿非常容易,大家基本上也就不往深裡走。我記得前兩年左右自己也還在學習時,曾寫了一篇文章探討什麼是茶會,當時茶會非常的流行,左一個茶會右一個茶會,當中很多茶會是展銷會,有的人賣杯子、有的人賣茶,因為大家都學會了「擺」-也就是我前面說的,淺層、形式上的模仿是最容易的。

但後續是一片混沌,除了人人都在辦茶會、擺茶席外,還學會了一套剛才葉老師講的「雞湯的氾濫」。我昨天也聊到,當你反應可能這茶有點問題時,對方一定會回答你:茶都是平等的,泡好泡壞並不重要。在我看來這是非常大的問題,我覺得這話背後有相當的歷史淵源,有時候我會開玩笑說「中國受禪宗的影響太深了,大家都見性成佛;受王陽明心學影響太深了,以至人人都是聖人。」其實大家是缺乏權威的,這和剛才何老師說的很像,因此很觸動我。中國現在能看到的大多數茶人,就算你沒有提出問題,也沒有開宗明義講,他也會不斷的說:我這是隨意茶,我隨手泡,你看我心裡,看到我的什麼?其實你什麼都沒看到,只看到一堆不好的茶一直泡,和不好看的茶具。你是看不到的什麼的,因為這裡面其實有非常嚴格的、剛才曾老師也說過的「第一步的、技術上的訓練」,而這些人可能連技術上的訓練都沒有完成。比如說一泡茶在攝氏八十五度的時候是什麼情況、而八十六度、九十一度或九十二度時會怎麼樣,都會呈現出非常微妙的變化。都沒有呈現出這一泡的訓練,因為我們太快了,這個階段全省略而直接進入下個階段,就是宣稱都是平等的,我覺得這個是中國現在特別明顯的現象,這個現象下去就是人人都覺得自己很高明,其實這件事也令我非常困惑,開始思考我寫的茶會究竟是什麼?

曾有位中國人寫過文章來批評我,他寫說「我們幾個人在菜場前隨便拿個茶壺泡了喝,那也叫茶會。」我覺得這問題很大的關鍵在於:我們其實不在同一個層面上討論問題。我們可以說精緻的喝茶和粗糙的喝茶有什麼區別,而「茶會是什麼?」這個問題依舊特別困擾我。今年初我曾到台灣找解致璋老師,我參加過解老師很多次的茶會,覺得她的茶會是不一樣的。那不同處在於,她不是像我們這樣大家臨時來了就準備,她可能會提前三個月,去瞭解周圍的環境如何、周邊是些什麼地方?泡茶該用哪種水溫、天氣會是晴雨等等,她會不斷的考慮,包括今天天氣比較悶熱或冷,茶湯溫度會因此有什麼改變。從表層來說,這樣的茶會主旨呈現出最美好的茶湯,而現在許多主辦茶會的人也都會從這一塊去補強,

再延伸下去,你就很簡單的提出一個問題:最安全、最好的泡茶方法,是永遠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嗎?像是永遠在自己家泡茶,在同一個地方泡個十年,用這裡的水、空間和環境,那肯定比隨便找一天來表現好很多。這個不用討論,你熟,在熟悉周圍環境、水溫和器物的控制下,當然可以做得很好。但是我覺得解老師也有她的好,她是在摸索、嘗試中得出來的,這裡並不多加陳述。比如說一開始在河邊泡,大家也許覺得在野外泡茶聽起來容易。尤其是今年春天,北京有很多廟宇內的樹開花,然後我們就可能去個兩百年的古樹下泡茶,這時候你才發現,這個事情會讓人捉襟見肘,你的水怎麼燒?你是碳燒?你是電壺燒?你用什麼樣的溫度?你能保證是什麼溫度?桌子是什麼樣的?你整個人從技術面上來說便不斷受到各種挑戰、制衡。其實今天我在這裡喝的茶,我都覺得還是粗糙的,這話並不是針對任何人,而是大家肯定不是真正的把心放在這裡,它根本不在。
而挑戰就是在這裡:你辦一個茶會是為了什麼?你辦一個茶會不是為了別人、也不僅是為了茶道,更多是為了自己。就像剛才曾老師所言,其實就是在說:泡茶到最後你能走到哪一步?我們現在聽起來,會覺得這種說法大家也講得有點多。

其實泡茶還真的就是面對自己,是看你是如何去修心的,中國很多人會把這道理掛在嘴邊,但都沒有跨向這一步,因為你沒有透過技術去修練、透過形式去修練,也沒有透過讀書、審美的形式去修練。以葉老師為例,很多人都透過媒體得知他有個園子,而我一開始看到,跟我現在去看到的園子絕對是不同的。可能我去了十次、二十次,我會有些疑問:老師你這棵樹為什麼放在這裡?其實背後都是有他的心思,他在想,我當年為什麼要在這裡種一棵樹?就像茶會,我為什麼要在這裡放茶碗,那並非只是個形式。
我覺得如何破除形式、回歸心靈,是一個特別重大的課題,而這個課題是沒有地域性的,整個東亞的文化系統中都有講述如何找到本我、建立自身,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說前面提到的那些紛紛擾擾、亂象,其實還都是表象;而如何找到自身,聽起來容易實際上蠻難的,現在的我也在不斷為此困擾。我不從事這行,但是我見到太多,必然會觀察,會逼自己去想一條新的路是什麼?我計畫想寫一本書,藉由茶會來表示一些茶界的回歸,其實茶,還有茶會,只有沉浸在裡面,它其實就會是一個非常險惡的東西,絕對不是風雅的東西,對每個人的挑戰太大了。
今年春天,我自己在戶外就泡過兩次茶,發現這事太難了,太需要面對自己了,沒有那麼多可以自鳴得意的東西。比如說你插盆花美不美?哪怕你學了十年,也沒那麼容易。總而言,我認為大家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,不分中國或台灣。
FOLLOW US
清香斋二号院